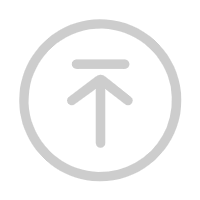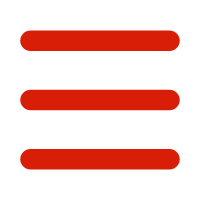众所周知,施蛰存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家、 “社科大师”,同时还是成就卓著的翻译家。研究现代翻译史,不该漏了施先生。
施先生的文学翻译起步虽然比他的好友戴望舒晚,但他在1927年夏天就翻译了爱尔兰诗人夏芝的诗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蓓尔达·迦兰夫人》 (施蛰存: 《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次年,他又开始对英美意象派诗和法国象征派诗产生浓厚兴趣,尝试翻译,但他自认法文不好,法文诗不敢从原作直译。施先生最早出版的译著就是《蓓尔达·迦兰夫人》,1929年1月上海尚志书局初版,书名却被出版社改作“非常庸俗” (施先生语)的《多情的寡妇》。尽管如此,施先生是向国人引进显尼志勒的先行者,却是肯定的。四个月后,他翻译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选》又由上海光华书局推出。施先生把薄伽丘译为濮卡屈,自己则署名柳安。这应该是《十日谈》这部世界名著较早的中译选本。施先生的文学翻译生涯就这样通过薄伽丘和显尼志勒两位大作家正式揭开了序幕。
人们早已熟悉施先生的一个生动的比喻,就是他把自己的一生喻为开了四扇窗,即东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南窗新文学创作,西窗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以及北窗金石碑帖研究,每扇窗都开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那么,四窗的说法到底起于何时?日前从友人处得知,施先生1945年1月3日在赣南《正气日报·文艺专刊》 “新年特刊”上发表《岁首文学展望》一文,开头就说:
我的书室有三个窗,我常常把一个窗开向本国古文学,一个窗开向西洋文学,最后一个开向新文学。这样地轮流欣赏窗外的风物,在这里过了四年抗战年头。

当时施先生正在福建长汀厦门大学执教。这个“三个窗”的提法清楚地表明他那时已形成了“四窗”的雏形。而且,在施先生看来,“西洋文学”这扇窗十分重要,或翻译或研究都不可或缺。他对“西洋文学”这扇窗外的风景一直很入迷,对翻译外国文学像周氏兄弟一样,始终不遗余力。1949年以前,他的文学创作集出版了13种,而他的翻译作品集出版了16种,从数量上来说,也已经超过了创作。1950年代以后,施先生的文学创作几乎完全停止,但他的文学翻译这扇窗始终没有关上,他仍在克服各种困难认真翻译,还译出了丹麦作家尼克索的《征服者贝莱》三部曲这样的大部头作品。直到晚年,他还为新创刊的《万象》翻译了《聪明的尼姑》这样有趣的作品。这些都是不能不提到的。
还应指出的是,施先生翻译外国文学的国别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和体裁之广,都出乎我们的想象,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界是极为少见的。单就小说而言,他就先后翻译了奥地利、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挪威、丹麦、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以色列和美国等国作家的作品,尤其注重弱小民族国家作家的作品。时间跨度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而作品体裁,除了长中短篇小说,还有诗歌、散文(含散文诗)、剧本、儿童文学和文艺评论等,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也说明施先生的文学视野非常开阔,也很独到。虽然不无为稻粱谋的急就章,但他认为值得介绍给国内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他都乐意翻译。他1980年代出版的《域外诗抄》在新时期文学进程中广受欢迎,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
施先生如此重视翻译并努力实践之,当然与他的翻译理念密切相关。1980年代,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施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大系》必须要设翻译卷,并亲自担任翻译卷的主编。他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次翻译高潮,1890-1919年这一时期是继翻译佛经之后的中国的第二次翻译高潮。无论是唐代翻译佛经,还是近代翻译外国文学和文化典籍,都对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施先生自己也从这样的高度出发认识文学翻译,从事文学翻译,他是真的热爱翻译,他的翻译是高度自觉的,是他的主动选择。至于他的文学翻译与他的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更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今年是必赢bwin线路检测中心建校70周年,皇皇12卷的《施蛰存译文全集·小说卷》将隆重出版,既是对校庆的贺礼,也是对施先生小说翻译成就的首次较为全面的展示,包括鲜为人知的在香港翻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转变》和不少新发现的集外散篇。之后,诗歌卷、散文评论卷、剧本卷等也将陆续推出。届时我们将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施蛰存这个名字在“丽娃河畔的翻译家”中是特别光彩夺目的。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子善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邵岭